杨靖︱知识的谱系:美国超验主义的德国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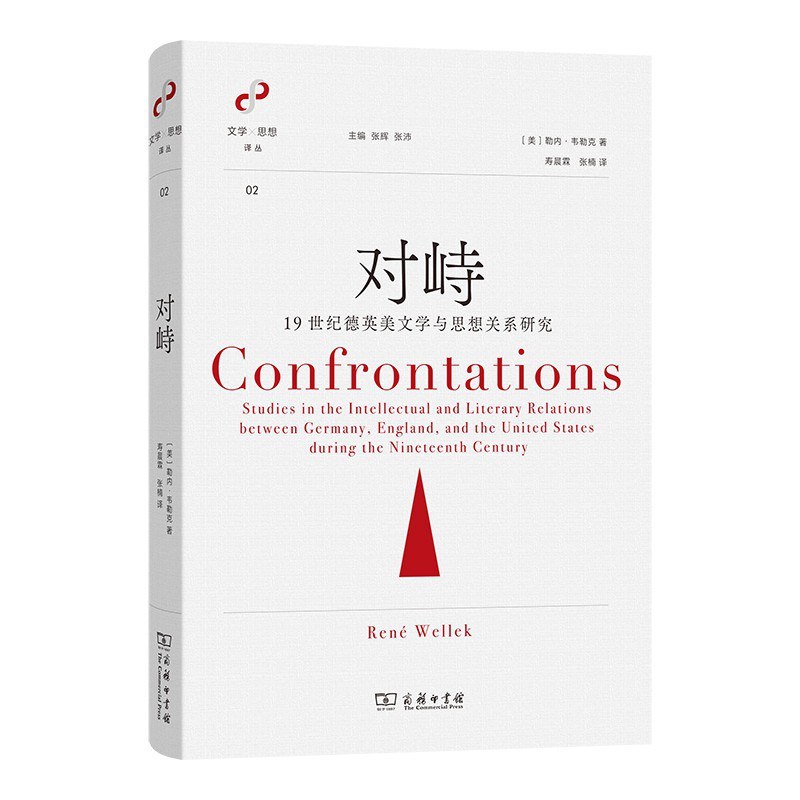
《对峙:19世纪德英美文学与思想关系研究》,[美] 勒内·韦勒克著,寿晨霖 / 张楠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7月版,235页,75.00元
超验主义是十九世纪中期前后美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然而,迄今为止,关于这场运动的思想渊源,却是众说纷纭:或认为它主要根植于新英格兰本土的虔信主义理念,或认为它主要受到英国浪漫主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而勒内·韦勒克在《对峙:19世纪德英美文学与思想关系研究》(寿晨霖、张楠译,商务印书馆, 2024年)一书中则以翔实的考据论证:美国超验主义(即F.O.马西森所谓“清教背景中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更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并非直接作用于美利坚的清教土壤,而是通过英国两位“德国思想供应商”——柯尔律治和卡莱尔——的译介和传播。
十八世纪末,德意志高等教育一枝独秀,由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以及哥廷根、耶拿等高等学府在古典文化、历史批评和哲学研究等领域声望卓著,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效法的对象——照韦勒克的看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美国未曾产生过任何创见”。爱默生的哈佛导师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和乔治·蒂克诺(George Ticknor)是最早赴德朝圣的美国留学生,爱默生的兄长威廉以及霍桑的好友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不久也加入这一行列。与此同时,代表先进文化的德语在新英格兰地区也成为热门“显学”:日后“超验俱乐部”(Transcendental Club)同仁如赫奇(Frederic Henry Hedge)、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帕克(Theodore Parker)、富勒(Margaret Fuller)皆熟谙德文,他们翻译、出版了若干德国浪漫派(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等人)的著作,为“德国热”推波助澜。有意思的是,1841年,富勒翻译谢林著名演讲《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bildenden Kunste zu der Natur),后来才发现柯尔律治在他本人署名的著作中早已对此做过“非常准确的意译”。受此时尚影响,爱默生决定自学德语以便“随时查阅德文原著”——据考证,爱默生此举主要受到斯塔尔夫人名著《论德国》的激发: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起,爱默生的日记中满是从《论德国》一书中抄录的格言和轶事,这些格言在他的首部著作《论自然》中占据了显著位置。与此同时,爱默生的邻人霍桑则尝试与新婚妻子索菲亚(Sophia Peabody)一道切磋“德语的词汇和文法”——霍桑的姻亲皮博迪小姐(Elisabeth Peabody)最早将“超验”一词引入美国知识界。
早在1820年代,由波士顿唯一神教(Unitarianism)领袖钱宁牧师创办的《基督教观察家》(Christian Examiner)开始刊载有关德国《圣经》“高等批评”(High Criticism)的系列文章——爱默生首篇论文“关于中世纪宗教的思考”(1822)即刊发于此。1834年到1835年间,该季刊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康德、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等人哲学思想的论文,这些论文对“当时人称超验主义者的年轻人解读《圣经》和领悟自然的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由此也导致学界对于超验主义的诞生日期聚讼不已——较早的文化研究学者将日期设定在1819年前后,即初代美国留学生从德国大学学成归来之日;后起的倡导“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说的学者则将其设定为爱默生在哈佛发表《美国学者》演讲(1837)之时,或超验主义的“福音书”《日晷》创办之时(1840)。然而,根据韦勒克的考证,这一时间节点被明确为1829年,即柯尔律治《思维之助》(Aidsto Reflection)在美国出版发行之日。借用F.O.马西森在《美国文艺复兴》(1941)一书中的论断:柯尔律治是“美国超验主义发展的最为直接的力量”,他的《思维之助》“拉开了爱默生思想的序幕”,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超验主义发展”。
1798年,出于对德国文化的仰慕,柯尔律治偕好友华兹华斯兄妹赴德访学。回国后,柯尔律治的兴趣逐渐由抒情歌谣转向哲学沉思。在《思维之助》(1825)一书中,柯尔律治借用康德哲学术语理性(Reason/Vernunft)和理解(Understanding/Verstand)对人类世界精神层面和自然层面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区分:他将理性视为一种超感官的直觉力量,它“既是道德的源泉,也是最高形式智力的源泉”;而将理解(力)视作较为“谦卑的仆从”,它整合、对比源自感官知觉的想法,帮助我们进行反思和概括。爱默生后来在日记中曾以天文学概念作譬喻来阐明二者的关系:理解(力)形成较小的本轮(epicycle),而理性则形成较大的均轮(deferent)——“心灵的原始法则……是理性的理念;它们让理解力感到震惊。”
柯尔律治是一位有书必读的饱学之士,对德国哲学和美学的近况了如指掌,对谢林的同一性哲学(philosophy of identity)更是推崇备至(但对谢林的两位图宾根神学院同学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无感)。照韦勒克的看法,柯尔律治在英国学界独步一时,和极少接触德文的华兹华斯、兰姆、哈兹里特等人“判然有别”:他不仅熟练掌握德国的辩证法体系和文艺理论方法,还通过大量著译和演讲将其引入英国学界。据统计,日后流行的文学批评术语,诸如心理学、美学,客观/主观,有机/机械,古典/浪漫,以及象征、寓意等,多半拜他所赐。更重要的是,柯尔律治的译介工作不但为英国批评家开辟出一条新路,而且也成为美国超验主义者思想的主要源头。《思维之助》出版数月后,富勒在日记中预言,“柯尔律治对未来若干个世纪的贡献……不可估量”。超验俱乐部早期成员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牧师曾经感慨:“我内心深处对原子论(atomism)这种试图脱离感受来诠释灵魂,并试图从物质中推导思维……的做法不无反感。所以我放弃了此类做法,直到我从柯尔律治那里汲取了康德的观点:知识虽始于经验,但并非直接来自经验。”
遗憾的是,向慕德意志文化的柯尔律治在英国本土并不受待见,相反却受到褊狭自大的岛国国民的百般嘲讽——与这位胸怀宽广的文化使者在美国受到的礼遇恰成鲜明对比。而他的思想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引发轰动效应,首先应当归因于时任佛蒙特大学校长詹姆斯·马什(James Marsh)的强力推介。马什读到柯尔律治的《思维之助》,相见恨晚,于是设法在美国重印此书,并为之撰写长篇《序言》。作为宗教人士,马什在《序言》中开宗明义,一方面将靶心瞄准“用洛克哲学语言曲解加尔文教义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另一方面则对当时各类文学作品在青年读者中未能产生足够正能量“深表遗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作品让读者对宗教原则漠不关心;查尔斯·兰姆的作品与之相较也不遑多让;尽管华兹华斯本人怀有崇高抱负(high thinking),但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内容更倾向于“模糊的自然主义或泛神论,而非传播福音的真理”。毫无疑问,马什大力推广《思维之助》一书,旨在引导美国国民将理智与情感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而实现个人的道德提升。
根据马什的阐释,柯尔律治笔下的“自我”(ego)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能量,比人性更高。这一“自我”所拥有的理性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故可推而广之适用于全人类。易言之,人之理性不同于人的理解力:前者能够洞悉任何感官经验无法感知的“真理”,而后者则可以通过适当的反思获得神谕般的(divine oracle)智慧,从而能够在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的最高形式中领悟理性的奥秘。所谓“思维之助”,一言以蔽之,即“心灵本身就是最崇高的反思对象”。而这一论断,也给美国超验主义者提供了无限遐想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美国著名学者奥德尔·谢泼德(Odell Shepard)将马什的《序言》称为“超验主义的旧约”。在谢泼德看来,尽管马什对柯尔律治关于“理性”和“理解”的区分纯属“误读”,然而这一“误读”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正是从这里,爱默生等人找到了自己思想的核心概念,即部分和整体、物质和精神、心灵和自然的有机统一(或称之为“超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同一性”)。由此马什断言,柯尔律治阐发的“不是理论,也不是臆测,而是生活。不是哲学生活,而是鲜活的生命过程”。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是美国语境中激情勃发的超验/浪漫主义对冰冷的启蒙运动及僵化的机械唯物论的有力反拨——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曾引威廉·布莱克名句:“一只知更鸟受困于樊笼,整个天堂陷入狂怒之中”,并断言此处的“樊笼”即指启蒙运动。
马什作序的《思维之助》出版后,超验俱乐部成员无不欢欣鼓舞。183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日耳曼敦任教的超验主义者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在书的每一页写下心得体会。后来他在日记中透露,阅读此书“开启了我精神生活和智力生活的新纪元”。另一位资深超验主义者赫奇也宣称它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并认为马什的“及时”(timely)工作为超验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多年后,赫奇在回忆录中写道:1836年9月,当超验俱乐部举行首次会议时,“爱默生先生、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和我……几乎所有成员都在阅读马什的作品。”正如彼得·卡拉菲奥(Peter Carafiol)在《超验理性:詹姆斯·马什与浪漫主义思想的形式》(Transcendent Reason: James Marsh and the Forms of Romantic Thought,1982)所言,十九世纪美国清教人士就知识“起源”问题掀起了一场文化运动,超验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马什厥功至伟:他的作品不仅比爱默生更具清教主义色彩,而且比爱德华兹更具浪漫主义色彩——它“表明了清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差距,而民族认同的神话旨在掩盖这一差距”。由此不难推断:“美国超验主义运动肇始于佛蒙特,而非康科德或波士顿。”
基于谢泼德等人的研究,韦勒克更进一步阐明,马什的阐释性文本属于双重“误读”:柯尔律治误读康德,而马什又误读柯尔律治。事实上,康德本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未将人的智性明确划分为“理解”和“理性”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较为近似的划分是朝向日常经验的“分析判断”以及超乎于此的“综合判断”——根据康德的论断,“分析判断”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在进行一种可靠而广泛综合时”所必需的手段(在中文语境中,前者可译为知性,后者则近于悟性)。然而这一区分之所以能够吸引超验主义者的眼球,是因为此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从一方面看,假设理性能够“通过直觉洞见宇宙的精神主宰和道德的超验基础,那么超验主义者就能够摆脱洛克经验论和苏格兰哲学对于人类认知的限制”;从另一方面看,德国哲学“将这样的超验维度内置于人的智性和主体性之中,这又使得他们可以不再依赖传统宗教提供的以人格化上帝和《圣经》为基础的道德哲学”。由此可见,正是基于“理性”和“理解”的区分,超验主义者才得以突破清教传统文化的束缚,从而为美国文明的长足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爱默生对这一充满思辨色彩的哲学学说拳拳服膺,而他本人也是最早接纳这套哲学辞令之人。1834年5月,在写给弟弟爱德华的信中,爱默生坦言:“现在我使用这些哲学概念,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像柯尔律治和德国人那样,在‘理性’和‘理解’之间做出区别。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哲学,而且就像所有的真理一样,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两年后,在《论自然》(1836)一书中,“理性”和“理解”的区分无疑已成为爱默生超验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名篇《论语言》中,爱默生宣称,在理解和认知的层面,我们将“人性中普遍性的灵魂”称之为理性;而在“判定它与自然界的关系时,我们称之为主宰自然的精神”。很显然,正如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在《爱默生传》(1932)中所言,爱默生欣然接受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康德的先验论)思想,乃是因为其精神气质与他一贯信奉的普罗提诺“太一”(The One)说一脉相承。
据韦勒克考证,爱默生及美国超验派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接纳除了通过柯尔律治(经由马什),另有一个渠道是通过托马斯·卡莱尔。像年长他一辈的柯尔律治一样,卡莱尔也是狂热的“德国文化粉”——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初,他译介的对象包括歌德、席勒、赫尔德,以及诺瓦利斯、蒂克、E.T.A.霍夫曼,还有让·保罗(卡莱尔宣称他本人的精神气质“更接近于让·保罗,而非歌德”),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德国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卡莱尔提出一种美国学者闻所未闻的历史使命,即“文人无需从事特定职业,也无需创作诗歌、戏剧或散文。真正的文学生活应如文学作品本身一样,向其时代和地方居民传达神圣理念”,并且断言“诗无非只是较高级的认识……是智慧的另一形式”——诗首先是一种认识,能够深入到表象后面的实在,能够洞悉宇宙的奥秘,因此,“真正的诗人是先知”。诸如此类的论断,令爱默生等人欣喜若狂。
当然,吸引爱默生的不仅是卡莱尔的浪漫文学思想,还有他疾风暴雨式的社会批判思想,这也是卡莱尔与宗教道德家柯尔律治最大的不同之处。作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卡莱尔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感到痛心疾首。他在《时代征兆》(“Signs of the Times”,1829)一文中大声疾呼:当下的时代特征是“机械横行,灵魂尽失”。人们拼命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但无人在意其精神疾患已病入膏肓——“我们被自己锻造的锁链捆绑着,问题是如何才能将其挣断”。而卡莱尔提出的解决之道也很简单:精神斗争是最有效的行动。换言之,一个人只需忠实记录自己的所感所思,通过不断反思实现个人精神生活的“自我培养”,就可以为社群(Community)提供最优服务。照末代超验主义者弗罗辛哈姆(O.B.Frothingham)的看法,尽管“卡莱尔的文章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布道文(sermons in disguise)”,但这一行动号召在渴望社会变革和道德进步的新英格兰却“点燃了所有年轻人的真诚之心”——柯尔律治提供了哲学思想,而卡莱尔则提供了“比哲学更佳……充满感情和目标的”行动指南,即韦勒克所谓“新型的世俗福音书”。
如果说马什从柯尔律治著作中吸纳的思想将伯灵顿派(Burlington,佛蒙特大学坐落于此)导向政治观念保守的神学超验主义,爱默生等人从卡莱尔作品中汲取的力量则将康科德派引向激进的社会超验主义。阿尔科特创办的“果园农场”(Fruitlands)和里普利创建的“布鲁克农庄”(Brook Farm)都是渴望社会变革的尝试——旨在摆脱限制个人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尽管上述社会改造计划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即基于平等理念、废除资本压榨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根据爱默生的“超灵”(Over-soul)说,内在的、精神的原则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础,同时这些原则也构成了“良知”或“理性”的基础,让每个人都有可能与精神世界联系起来。当一个人因此而摆脱(或超越,transcend)对世俗低级领域的忧虑和关注时,他就会接触到这种精神原则,并以这种精神原则来指导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验主义堪称美国清教土壤中开出的一朵“奇葩”——其核心是颂扬每个灵魂的神圣平等,主张民主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鼓吹人人皆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
在这一社会理想激励下,爱默生大声预言:“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就是一首诗;它幅员广大,想象力沐浴着它的光辉,缺乏韵律不会使它无所作为。”尽管爱默生本人未能写就雄浑壮阔的美国诗篇,然而他的超验主义门徒惠特曼却实现了他的宏愿。《草叶集》问世之前,惠特曼坦承他受到赫尔德《民歌集》(Volksliede)的启发和影响,并声称他“已拜读康德,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四大名家。随后,这位以“德国哲学最伟大的诗歌代表”自居的美国头号诗人倡言,美国人要努力创造一种彻底的民主,这一信念是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表达”,并且应当使之“成为宏大宇宙史的目标”(佩里·米勒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惠特曼本人的诗集堪称“唯心主义之歌”——从某些方面看,《草叶集》的创作始末不仅“契合‘四大名家’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伟大体系的发展……而且旨在证明,精神界与物质界,具有基本同一性”。这一段文字,在笔者看来,恰好可充作韦勒克“19世纪德英美文学与思想关系研究”(本书副标题)的上佳注脚。
据韦勒克在本书卷首交代,他写作《对峙》的初衷,是要和洛夫乔伊(A.O.Lovejoy)进行商榷——后者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一个国家的‘浪漫主义’可能与另一个国家的‘浪漫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韦勒克的谱系学研究表明,德英美等国的文学思想不仅颇多共同之处,而且渊源甚深。同时,这一纵横交错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对于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浪漫主义、超验主义等),若要全面、透彻地加以了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方法同样重要。